简女的辩护律师邱荣英引述「修复式司法报告」中,其先生白男于修复程序中与司法人员的对话内容。白男表示,婚前他曾在中国工作,婚后则与简女一同开业、做电商,直到后来简女遭到事业合伙人伤害导致失明,并考量到孩子即将开学,因此举家搬到台湾与公婆同住。
白男指出,简女的湖南娘家务农,可能因此想法较传统,认为女儿失明一事「很晦气」,也因此全家回到台湾后,简女也非常努力融入他的家庭,对于公婆也尽力适应,照顾小孩更是无微不至,若让他对老婆打分数「会是100分」。
不过,谈到夫妻间的重大转变,白男认为与一开始对公婆隐瞒失明一事有关,让他与简女都颇有压力。白男解释,2人因为害怕公婆知道后,会了解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状况,且当时中国那边也正在打官司,加上他返台后并没有外出工作,双方对于经济压力的感知出现落差,导致夫妻关系的裂缝加深。
此外,白男认为也与公婆的要求有关。白男表示,针对家人间的冲突,简女总是直接向公婆沟通,相较之下,他的父母反而处理得不好,一直希望透过儿子(即白男)作为沟通桥梁,而他自认,他的父母比较传统,就是希望简女按时起床、打扫家里,且简女也始终迎合,照顾小孩更是不用多说。
眼见简女与公婆口角扩大,白男后来曾向父母表明简女有受伤的情形,双方的争执才一度有和缓迹象。直到此案发生隔天,他发现小孩不见了,一家4口的护照也不见了,一开始还以为是简女带著小孩回到中国;案发后,白男也始终认为老婆是带著小孩去轻生,因为以简女那么关爱小孩的想法,他一直相信简女是去轻生。
白男有感而发,在简女羁押于看守所期间,他曾送了3张小孩的照片、3本孩子读的书给简女,即便他自身并无信仰,直到现在他都以诵念佛经的方式陪伴已逝的小孩,也让简女在看守所中念经。话锋一转,白男坦言在与老婆会面时,2人从来没有聊过此案,但他认为孩子的母亲活了下来,是因为「孩子救了她」。
白男直言,面对今天这样的结局,他始终有点埋怨,若非简女娘家未给予支援,举家搬回台湾从来就不是首选;若简女娘家愿意照顾女儿或妈妈,他就可以放心地工作,但因为丈母娘不同意,且简女的湖南老家也时常闲言闲语,认为这是「不幸事件」。
事发至今,白男坦言已很少和父母说话,如今他只想把这起事情简化为两条线,一条是自己和孩子们,另一条则是简女与孩子们,而之所以这么划分,是因为他自认想拿掉一些怨跟恨;至于他的父母,他只希望父母能找到自己的方式去面对。
白男也同意参与修复式司法,他认同「所有的原谅可能是若干年后,而非现在」,因此希望寻求以科学理性的方式面对本案,而他也不觉得自己能被称为「受害者家属」,反而是「加害者」。如今,白男不想去追究本案发生的原因,因为「生者心不安,死者就会不安」,他希望简女能够安心面对自己的良心。
白男希望法官能酌情量刑,也想知道他与简女身为「加害者」该如何面对被害者,同时他也没有指责简女,因为他认为这是「他们这一代人」的事情,若众人间出现指责只会让小孩们变得不幸,而他也不想让小孩被贴上「找上不好父母」的标签;若真要说恨谁,他只恨「我自己」。
至于现在对于简女有什么感觉?白男坦言「现在对她找不到任何的感觉」,对他而言,简女就是个需要帮助的「陌生人」。作为丈夫,他也想跟太太说:「永远不要觉得我们家破人亡,我在、孩子也在,还是要把孩子带好。我们可以让众人指责我们是失败的父母,但不希望孩子们被认为是『不幸』;除了2024年7月2日那天,孩子们都很幸福。」
难掩激动情绪,简女在法庭上听著丈夫复杂的思绪,数度拿下口罩啜泣不止;在最后听见先生的喊话后,简女的情绪也随之溃堤,坐在被告席上泣不成声,更伴随著阵阵干呕,只见律师在一旁不断安抚简女「深呼吸、深呼吸⋯」,法官谕知休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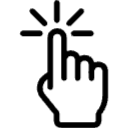 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