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峡报导,在新加坡芽笼一个潮湿的星期二早晨,58岁的塞琳(Serene,化名)照例揹著帆布袋,走进一条条狭窄的巷弄。在第16巷附近,她看到两名女子站在店屋外。
她用中文开口说:「我以前没看过你们,你们是刚到吗?」
其中一人露出有点戒备的微笑:「上个星期。」
她们聊起家乡和食物,回答一开始都很简短,直到塞琳问她们打算待多久,「就几个星期,」那名女子说完,补了一句:「我不会逾期停留。妳是警察吗?」
塞琳笑著否认:「不是啦,我只是在这一带工作。」她说著,把一小包芭乐辣片塞进对方手里。
塞琳任职于基督教团体,已经在当地红灯区关怀超过10 年,她把自己的角色看作单纯「表达关心」,「我们不是来『拯救谁』的」,「但如果看起来有人很烦恼,我们就会问,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」
她每周看到的画面——短短的对话、带警戒的微笑、来来去去的女人——其实都连向一段更久远的历史:要理解她今天做的工作,就得回头看,新加坡性交易是如何从殖民地时期一路发展下来的。
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研究,新加坡约有 8,030 名女性性工作者。
1826年人口普查显示,新加坡当时只有 13,750 名居民,却已呈现严重性别失衡:华人男性 5,747 人,华人女性只有 341 人;印度男性 2,208 人,女性只有 40 人;马来男性 2,501 人、女性 2,289 人。
这份普查凸显了当时新加坡作为快速成长、男性占压倒多数的港口城市,对性工作者有多大的需求。
到了 1884 年,新加坡已有约 6万名华人男性,却只有 6,600 名华人女性,其中约 2,000 名广东和潮州女子在妓院工作。
有学者推算,19 世纪末抵达新加坡的年轻华人女孩中,多达 80% 最后被卖进妓院。
有些女性是自己选择进入性交易,但更多人是被贫穷推著走,或直接被家人卖掉。来自中国和日本乡村的年轻女性,先途经长崎、广州等港口,再被送往新加坡的妓院。
到 1905 年,中路(Middle Road)甚至被称为「小日本」。官方纪录显示,当地密集分布著 109 间妓院,里头共有 633 名日本女子工作。
在性交易快速扩张下,殖民政府最后放弃「全面禁止」的做法,转向「管制模式」,发牌管理妓院、规定医疗检查,并透过 1870 年颁布的《传染疾病条例》=订下营业规则。
这种「不完全禁止、改以规范」的殖民治理思维,也延续到今天,形塑出新加坡既承认又限制性产业的复杂法律框架。
根据前述 2023 年研究,在约 8,030 名女性性工作者当中,大约 800 至 1,000 人在芽笼主要红灯区内、超过 100 间受管制的妓院工作。这组数字并非官方统计,而是由前性工作者、以及每周到现场的志工外展员,以经验推估出的范围。

不过,这些「有牌照的妓院」只是整体样貌中的一小部分。更庞大的地下经济远远超出芽笼巷弄,延伸到按摩店、KTV、沙龙、应召仲介,甚至包括私密聊天频道和 OnlyFans 等订阅制平台,构成一整个线上线下交错的市场。
即便如此,数字依旧非常「不稳定」。研究只估算了女性性工作者,并未把男性与跨性别工作者、在旅馆或公寓单打独斗的「自由职业者」、规模很小的自组团队、或被仲介「抽成」管理的工作者纳入,所以真正的产业规模,很难被完全看清。
研究指出,多数性工作者是短期移工,以观光签证入境、停留几星期就离开;新加坡公民与本地居民只占很小一部分。本地人(包括永久居民和长期探访签证持有人)大约只占整体从业人口的 15% 至 20%。
非营利组织 Project X 执行董事贺(Vanessa Ho)说,要精准说出她们「为何进入这个行业」并不容易,因为光用「性工作者」三个字,其实也遮蔽了很多现实,「一位单亲妈妈的故事,和一位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故事会完全不同;从印尼来的,又会跟从中国或越南来的有巨大差异。大家的故事复杂得多,也细腻得多。」
她认为,把这些人唯一地拼成「被害者」或「道德问题」,忽略了她们共同面对的结构性压力:债务、照护负担、薪资停滞、保护不足,以及一个残酷的现实——「这份工作确实能赚到钱」。
在新加坡,受管制的妓院会被官方监测健康与安全,里面的性工作者必须定期接受性病与爱滋病毒检查,并实施「100% 必须使用保险套」的政策,虽然实务上严格执行到什么程度,外界很难得知。
新加坡的性产业地图也不止于芽笼,长年被称为「小泰国」的黄金坊,在 2023 年 5 月拆除重建前,曾是泰国移工聚集的夜生活据点;印度与孟加拉移工则多出现在小印度区的德加路(Desker Road)一带。
直到许多店家在 2023 年失去公众娱乐执照之前,乌节大厦(Orchard Towers)也以酒吧、夜店与灯红酒绿的形象闻名。
在这些社区背后,存在著各式各样的非正式安排:在网路上自我宣传的自由接客者;视情况提供「额外服务」的按摩师;在表演与亲密工作之间游走的酒店小姐;以及门面看似普通、走进第二道门后就变成另一个世界的店铺。这些不断变动的聚点,拼出新加坡性产业的地理版图,也紧扣著不同移民潮与市场需求。
至于红灯区对社区影响,有男性居民抱怨自己在街上被站壁女郎主动搭讪、直接报价;也有女性居民被误认为性工作者。居民同时担心,KTV 营业到凌晨 3 点带来的噪音与酒驾问题,已影响社区安全。
同一时间,性工作者的组成也在变化:有人是「推到签证边界」的观光客;有人是拿特别长期准证、为了补贴不稳定收入而兼职;也有人像 40 岁印尼籍永久居民黛薇(Dewi),选择这份工作,是看重它的弹性——既能顾小孩,又能在先生收入不足时分担家计。
尽管「性交易」本身没有被明文禁止,但它周边的很多行为却是违法的:招揽嫖客、在无效签证下工作、皮条客行为、经营无牌照妓院等。这造就了一个很窄的缝隙——一小部分在「受管制」的框架下运作,其他人则随时面临取缔。
贩运的征兆;一旦发现有表面上的犯罪事实,才会进一步展开调查。
当有交易纠纷发生,弱势的往往还是性工作者,某一起案件是性工作者报案指控客人拒付约定款项,还施以暴力。最后,客人确实被起诉并判刑,但这名报案人却被关了 10 小时、手机被没收,还被要求留在新加坡 3 个月配合侦讯,在这段期间只能睡在非营利组织办公室的沙发上。
面对这样的代价,很多受害者最后选择沉默。
当案件浮上台面时,也往往揭露非法性工作者在皮条客与客人手中遭受的剥削。2019 年,一名堆高机司机周在 KTV 结识一名越南籍表演者,声称愿付 200元新币(约4,700元台币)到家中发生性行为,却在事后拿刀恐吓并强暴对方,最后被判刑 14 年、鞭刑 24 下。
2021 年,新加坡籍仲介陈男因剥削多名泰国籍性工作者,被判刑 15 个月,他替她们安排住宿,收走护照,要求她们「做满合约」才能拿回证件,并额外收取 1,200 元(约2.8万元台币)「赎回费」,借此阻断她们离开的可能。
黛薇同样对临检保持高度警戒。她工作的按摩店 24 小时营业,但多数性工作者会在早上接近中午才上工,待到深夜,轮流排早班。有散客上门,但店里更偏好熟客,价格在发生任何行为前就谈好,「一定戴套」是铁则。
即便她是永久居民,在无牌妓院工作仍是一项足以颠覆她人生的罪名。她对家人隐瞒工作细节,希望再做几年就能抽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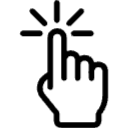 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






